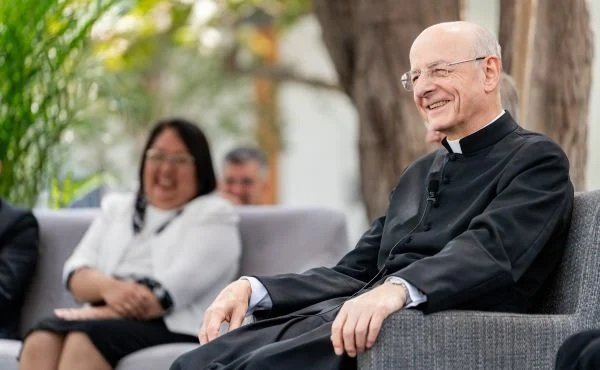當前共議制 Synodality 主教會議的主題之一,是平信徒在教會中的角色。鑑於平信徒在主業團的訊息、使命和靈修中都居核心地位,主業團能對這些反思有什麼貢獻?
平信徒在教會中的主要角色不是在教會結構中擔任職位;相對於整體而言,自然只會有少數人擔任這些職位(其中一些可能是必要的)。這個在共議制會議對話中出現的想法,在主業團的神恩中本來就已非常的明顯:每一位領過洗的平信徒都能體認自身使命的崇高與美好。正如早期的基督徒那般,當今福傳事業的未來重任,尤其落在與牧者共融團結的平信徒肩上。
教會的主要本質不在於教堂或建築物,而在於藉著洗禮與基督結合為一的子民。一位將耶穌基督銘刻於心、融入生活方式的平信徒,將在鄰里社區、親友、信徒與非信徒之中,體育、娛樂領域,以及各類專業、社會、文化、科學、政治與商業領域,成為教會鮮活而開放的見證。
教宗方濟各在宗座勸諭《你們要歡喜踴躍》中,闡述平信徒的核心地位時指出:我們應發掘「鄰人身上的聖德——那些與我們比鄰而居、反映了天主臨在的人。」自創辦之初,主業團便致力朝此方向邁進:它提醒我們,人人憑藉他的美德與缺點,能成為天主向眾人伸出的手,甚至觸及那些可能永遠不會踏進教堂之人。
正因如此,我認為投入時間與心力培育及靈性陪伴普世的信徒——這些在自身環境中實踐使命的真正使徒—— 是關鍵性的挑戰。這是教會一般工作的優先要務,感謝天主,這使命已在數千個堂區與各項行動中落實。
為什麼這種平信徒的身份對主業團作為一個機構和靈修途徑是這麼的重要?
其重要性在於聖施禮華理解這是天主對他的要求:生活在世俗中,透過平凡的現實—尤其是家庭與工作—闡明、展現、發掘並提醒世人那普世性的成聖召叫。創辦人最初為了推動主業團的事工,透過陪伴學生與專業人士、組織團體、祈禱並邀請多人的代禱。他更帶領這些青年探訪馬德里的貧病者,並舉辦靈修退省與培育課程。這精神隨後傳播到具有多元文化的許多國家,觸及各階層背景的人群。
上主與教會要求我們守護這神恩,並使它結出豐碩的果實。正如我所言,在家庭與職場中、在社會中心進行福傳,社會總會遭遇到重大的挑戰,如戰爭、貧困、疾病等。正是在這些現實中生活的普通信徒,才能見證基督如何臨在於他們生命中,如何推動他們成為不同的個體,並轉化所處的環境。因此,作為機構的主業團提供培育、陪伴及具體的靈修,專為肩負家庭的責任、繁忙的工作、面臨經濟的困境與遷徙等挑戰的男女而設。有些人領悟此精神後,感受到神聖的召喚,願意透過自己的生命來傳播這精神。
1946年,當聖施禮華首次為主業團尋求教會法的核准時,他被告知他早來了一個世紀。隨著主業團當前正在進行的教會法改革,您認為這些話仍然適用嗎?
1946年,主業團在四個國家成立中心,其理念尚不為人所熟知。即便在當時,成員也僅由幾位神父與絕大多數的平信徒組成。創辦人的宣講與教會主流思想相悖,他鼓勵平信徒在世俗中追求聖德,將福音帶入各行各業與生活場域。儘管他的理念深植於福音精神,卻顯得超前於那個時代。如今,主業團活躍於七十餘國,其精神更獲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全面的接納並推廣。與此同時,現行法規在應對新牧靈現象時顯露的困境亦不容忽視。或許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所期盼的平信徒為主角的地位,仍有漫長的路途待走。除此之外,我可保證教宗要求現行章程的修訂,始終秉持著「契合神恩」的根本準則——如今在許多地區,人們對此神恩的理解與共融已日趨深化。法律,這項如此必要的存在,卻應遵循著生命,遵循道成肉身的福音,以支持生命並賦予其延續性。
歐洲、美國,以及程度較輕的拉丁美洲,正迅速走向世俗化。主業團在全球許多最大且最世俗化的城市中都有據點。在這些社會中,主業團如何成為教會忠實的見證人,並在這些環境中傳揚福音?
2017年3月3日,我首次獲得教宗方濟各的接見。會晤中,教宗向監督團的成員提出一個具體的要求:請我們優先關注一個邊緣群體——遠離天主的中產階級與專業人士。這項優先方針既不排斥任何人,更開闢出廣闊而振奮人心的傳教視野,與即將到來的「希望禧年」精神高度契合。
主業團致力於在這些世俗化的環境中發揮影響力,並透過教育或慈善的創意行動提供全面培育。然而,最關鍵的並非是這些行動或組織架構,而是在於給予培育的成員,以及參與其使徒工作的數十萬信友:每位主業團成員皆在內心追求與天主的親密友誼關係,並透過人際網絡將這份情誼傳遞出去。值得注意的是,自教會創立之初,基督徒便在不同情境中傳揚福音:有些是在擁有深厚宗教傳統的環境中,正如我們在福音書中所見,有些則是在缺乏此類傳統的環境中。這份歷史現實猶如一盞明燈,能賦予我們信心,因為我們能從宗徒時代教會的實踐中汲取豐富啟示。
簡言之,針對當今時代,我們可借用聖施禮華的話語,將主業團使命的核心精髓歸結為:與每位男女建立友誼與信賴。與天主的恩寵合作,幫助人們和國家與基督相遇,用人對人、一對一的方式。無論何處,特別在世俗化現象更為顯著的地區,我們更需信賴天主的助佑,並透過自身的生活方式與多元化的行動彰顯這份力量。每位基督徒皆蒙召彰顯與天主同在、在天主內生活的吸引力;主業團致力支持那些實踐此使命的人。
主業團似乎面臨許多持續的挑戰,包括章程改革、托勒斯特朝聖地的處境、多篇由前成員撰寫批評它的文章、書籍及紀錄片,以及針對阿根廷43名前獨身助理成員投訴的司法調查。這是否是主業團歷史上最艱難的時期?它如何處理前成員的投訴?
主業團即將邁入百年歷史,此刻正是回顧其起源、審視至今歷程的良機。這正是持續學習、修正不足、在當下尋得喜樂、規劃未來的最佳途徑。
在此背景下,你提及的「持續性挑戰」,亦是呼喚我們徹底檢視:我們是否充分展現了此神恩的優美之處,同時在哪些領域可能存在適應性不足的問題,進而調整非核心事項,正如創辦人本人所言,這本是任何活著的有機體生命的一部分。
如我先前所述,章程修訂工作進展很順利,我們亦衷心期盼針對托勒斯特朝聖地的分歧意見能達成合宜解決方案,此事現正由聖座審理。
你提及的每一本書、每一篇文章或紀錄片,都令我們深感責任重大,因為它們承載著某人的痛苦或挫折。你或許能理解,我們努力工作的初衷,正是為了消除這些痛苦的根源,另一方面,我們期盼投身於這項使命能成為喜樂的源泉,正如它如今已成為數以萬計人們的喜樂,這一切皆是蒙天主恩典。然而,我們終究會犯錯,因為我們是由普通人組成的機構。我們自然希望及時發現這些錯誤並盡可能予以修正。
同時,批評——即使與事實不符——也可能成為我們發現可改進之處的助力。儘管這些批評未必令人愉悅或總是公正,有時卻能成為自我檢視的契機,偶爾更能促成內在的成熟。以平靜與信任之心面對需要改進或修正之處,始終至關重要。
關於你提及的阿根廷申訴案件,當地已成立聽證委員會。憑藉此經驗,我們創立首個療癒與調解辦公室,致力解決每件個別的衝突。能與眾多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令我們深感欣慰,這也使我們得以提出具體而個人的寬恕請求。廣泛的聽證機制,緩解了那些曾隸屬機構、或曾尋求機構協助與陪伴卻未獲回應者的傷痛。這項開啟療癒進程的工作完成以後,我們也在其他國家建立類似的程序。
我們由衷愛著所有曾屬於主業團的人們,無論他們因何種原因離開,我們都誠摯感激他們在主業團期間所做的善行,以及他們至今持續付出的善行。我們對每位成員都懷抱極大的敬意,因為他們當初決定加入主業團時,懷抱著將生命奉獻給天主的渴望。在多個場合中,我有機會向那些因缺乏愛德、正義或其他原因而心懷創傷的人們請求寬恕。在許多其他場合,我見證了他們對在主業團中度過的時光,以及所獲得陪伴的感激之情,這促使他們持續參與靈修與培育活動。過去一年間,我們幾乎每日都收到曾屬於主業團的人再度要求加入:生活證明,現實遠比我們根據過度二元對立,或兩極化的敘事所能想像的更為豐富多元。
在某些媒體,特別是美國媒體中,主業團被指控策動極端保守派陰謀,企圖讓唐納德·川普當選總統等諸多指控。對此您有何回應?
對此我無法多說,因為這純屬虛構。在主業團中,我們從不向任何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政治建議或指令:若有人如此行事,其他的成員必將反抗,因這違背我們的精神。優秀的天主教徒會根據自身的理念投票給不同的政黨與候選人。我決不會告訴他們該投給誰、支持誰或推動何種主張,主業團任何成員也決不會這麼做。同樣也是不恰當的,如果在培育的活動中,我們營造「主業團成員僅有一種合法選擇」的氛圍,即便是間接的暗示。熱愛自由即意味著熱愛多元性。
在你提及的媒體中,存在著諸多假設與陰謀論,甚至指名道姓地提及某些人士,然而他們並非主業團成員。我確信他們都是優秀的天主教徒,但這些媒體純粹是操弄真相,企圖將教會的機構牽扯進政治事務。
同時,我期盼世人能更理解平信徒在政治、社會及文化事務上的自主權…面對公眾事務時,每位基督徒皆有責任依循教會的社會教義塑造良知,詳盡瞭解各政黨候選人的政見,思索最符合共同福祉的選擇,並自由判斷。正因如此,主業團的靈性陪伴工作從不干涉成員在世俗事務上的正當抉擇。尊重參與政治的平信徒(無論是否屬於主業團)之自主權至關重要:其是非對錯應由個人承擔,而非教會之責。將信徒的文化、政治、經濟或社會倡議歸因於主業團或整個教會,實屬神職主義。
閱讀 The Pillar 發表的訪談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