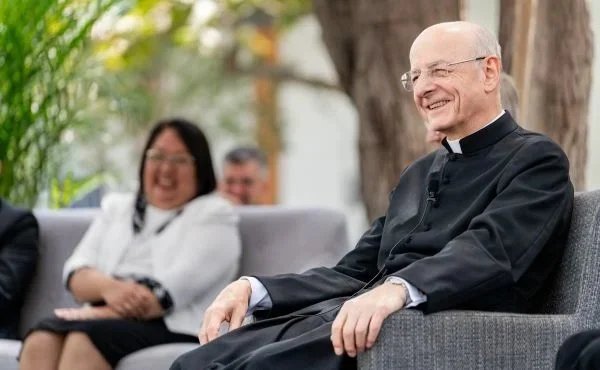当前共议制Synodality主教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平信徒在教会中的角色。鉴于平信徒在主业团的信息、使命和灵修中都居核心地位,主业团能对这些反思有什么贡献?
平信徒在教会中的主要角色不是在教会结构中担任职位; 相对于整体而言,自然只会有少数人担任这些职位(其中一些可能是必要的)。这个在共议制会议对话中出现的想法,在主业团的神恩中本来就已非常的明显:每一位领过洗的平信徒都能体认自身使命的崇高与美好。正如早期的基督徒那般,当今福传事业的未来重任,尤其落在与牧者共融团结的平信徒肩上。
教会的主要本质不在于教堂或建筑物,而在于藉着洗礼与基督结合为一的子民。一位将耶稣基督铭刻于心、融入生活方式的平信徒,将在邻里社区、亲友、信徒与非信徒之中,体育、娱乐领域,以及各类专业、社会、文化、科学、政治与商业领域,成为教会鲜活而开放的见证。
教宗方济各在宗座劝谕《你们要欢喜踊跃》中,阐述平信徒的核心地位时指出:我们应发掘「邻人身上的圣德—— 那些与我们比邻而居、反映了天主临在的人。」自创办之初,主业团便致力朝此方向迈进:它提醒我们,人人凭借他的美德与缺点,能成为天主向众人伸出的手,甚至触及那些可能永远不会踏进教堂之人。
正因如此,我认为投入时间与心力培育及灵性陪伴普世的信徒—— 这些在自身环境中实践使命的真正使徒—— 是关键性的挑战。这是教会一般工作的优先要务,感谢天主,这使命已在数千个堂区与各项行动中落实。
为什么这种平信徒的身份对主业团作为一个机构和灵修途径是这么的重要?
其重要性在于圣施礼华理解这是天主对他的要求:生活在世俗中,透过平凡的现实—尤其是家庭与工作—阐明、展现、发掘并提醒世人那普世性的成圣召叫。创办人最初为了推动主业团的事工,透过陪伴学生与专业人士、组织团体、祈祷并邀请多人的代祷。他更带领这些青年探访马德里的贫病者,并举办灵修退省与培育课程。这精神随后传播到具有多元文化的许多国家,触及各阶层背景的人群。
上主与教会要求我们守护这神恩,并使它结出丰硕的果实。正如我所言,在家庭与职场中、在社会中心进行福传,社会总会遭遇到重大的挑战,如战争、贫困、疾病等。正是在这些现实中生活的普通信徒,才能见证基督如何临在于他们生命中,如何推动他们成为不同的个体,并转化所处的环境。因此,作为机构的主业团提供培育、陪伴及具体的灵修,专为肩负家庭的责任、繁忙的工作、面临经济的困境与迁徙等挑战的男女而设。有些人领悟此精神后,感受到神圣的召唤,愿意透过自己的生命来传播这精神。
1946年,当圣施礼华首次为主业团寻求教会法的核准时,他被告知他早来了一个世纪。随着主业团当前正在进行的教会法改革,您认为这些话仍然适用吗?
1946年,主业团在四个国家成立中心,其理念尚不为人所熟知。即便在当时,成员也仅由几位神父与绝大多数的平信徒组成。创办人的宣讲与教会主流思想相悖,他鼓励平信徒在世俗中追求圣德,将福音带入各行各业与生活场域。尽管他的理念深植于福音精神,却显得超前于那个时代。如今,主业团活跃于七十余国,其精神更获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全面的接纳并推广。与此同时,现行法规在应对新牧灵现象时显露的困境亦不容忽视。或许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期盼的平信徒为主角的地位,仍有漫长的路途待走。除此之外,我可保证教宗要求现行章程的修订,始终秉持着契合神恩的根本准则—— 如今在许多地区,人们对此神恩的理解与共融已日趋深化。法律,这项如此必要的存在,却应遵循着生命,遵循道成肉身的福音,以支持生命并赋予其延续性。
欧洲、美国,以及程度较轻的拉丁美洲,正迅速走向世俗化。主业团在全球许多最大且最世俗化的城市中都有据点。 在这些社会中,主业团如何成为教会忠实的见证人,并在这些环境中传扬福音?
2017年3月3日,我首次获得教宗方济各的接见。会晤中,教宗向监督团的成员提出一个具体的要求:请我们优先关注一个边缘群体—— 远离天主的中产阶级与专业人士。这项优先方针既不排斥任何人,更开辟出广阔而振奋人心的传教视野,与即将到来的「希望禧年」精神高度契合。
主业团致力于在这些世俗化的环境中发挥影响力,并通过教育或慈善的创意行动提供全面培育。然而,最关键的并非是这些行动或组织架构,而是在于给予培育的成员,以及参与其使徒工作的数十万信友:每位主业团成员皆在内心追求与天主的亲密友谊关系,并透过人际网络将这份情谊传递出去。值得注意的是,自教会创立之初,基督徒便在不同情境中传扬福音:有些是在拥有深厚宗教传统的环境中,正如我们在福音书中所见,有些则是在缺乏此类传统的环境中。这份历史现实犹如一盏明灯,能赋予我们信心,因为我们能从宗徒时代教会的实践中汲取丰富启示。
简言之,针对当今时代,我们可借用圣施礼华的话语,将主业团使命的核心精髓归结为:与每位男女建立友谊与信赖。与天主的恩宠合作,帮助人们和国家与基督相遇,用人对人、一对一的方式。无论何处,特别在世俗化现象更为显著的地区,我们更需信赖天主的助佑,并透过自身的生活方式与多元化的行动彰显这份力量。每位基督徒皆蒙召彰显与天主同在、在天主内生活的吸引力;主业团致力支持那些实践此使命的人。
主业团似乎面临许多持续的挑战,包括章程改革、托勒斯特朝圣地的处境、多篇由前成员撰写批评它的文章、书籍及纪录片,以及针对阿根廷43名前独身助理成员投诉的司法调查。这是否是主业团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 它如何处理前成员的投诉?
主业团即将迈入百年历史,此刻正是回顾其起源、审视至今历程的良机。这正是持续学习、修正不足、在当下寻得喜乐、规划未来的最佳途径。
在此背景下,你提及的「持续性挑战」,亦是呼唤我们彻底检视:我们是否充分展现了此神恩的优美之处,同时在哪些领域可能存在适应性不足的问题,进而调整非核心事项,正如创办人本人所言,这本是任何活着的有机体生命的一部分。
如我先前所述,章程修订工作进展很顺利,我们亦衷心期盼针对托勒斯特朝圣地的分歧意见能达成合宜解决方案,此事现正由圣座审理。
你提及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或纪录片,都令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因为它们承载着某人的痛苦或挫折。你或许能理解,我们努力工作的初衷,正是为了消除这些痛苦的根源,另一方面,我们期盼投身于这项使命能成为喜乐的源泉,正如它如今已成为数以万计人们的喜乐,这一切皆是蒙天主恩典。然而,我们终究会犯错,因为我们是由普通人组成的机构。我们自然希望及时发现这些错误并尽可能予以修正。
同时,批评—— 即使与事实不符—— 也可能成为我们发现可改进之处的助力。尽管这些批评未必令人愉悦或总是公正,有时却能成为自我检视的契机,偶尔更能促成内在的成熟。以平静与信任之心面对需要改进或修正之处,始终至关重要。
关于你提及的阿根廷申诉案件,当地已成立听证委员会。凭借此经验,我们创立首个疗愈与调解办公室,致力解决每件个别的冲突。能与众多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令我们深感欣慰,这也使我们得以提出具体而个人的宽恕请求。广泛的听证机制,缓解了那些曾隶属机构、或曾寻求机构协助与陪伴却未获回应者的伤痛。这项开启疗愈进程的工作完成以后,我们也在其他国家建立类似的程序。
我们由衷爱着所有曾属于主业团的人们,无论他们因何种原因离开,我们都诚挚感激他们在主业团期间所做的善行,以及他们至今持续付出的善行。我们对每位成员都怀抱极大的敬意,因为他们当初决定加入主业团时,怀抱着将生命奉献给天主的渴望。在多个场合中,我有机会向那些因缺乏爱德、正义或其他原因而心怀创伤的人们请求宽恕。在许多其他场合,我见证了他们对在主业团中度过的时光,以及所获得陪伴的感激之情,这促使他们持续参与灵修与培育活动。过去一年间,我们几乎每日都收到曾属于主业团的人再度要求加入:生活证明,现实远比我们根据过度二元对立,或两极化的叙事所能想象的更为丰富多元。
在某些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中,主业团被指控策动极端保守派阴谋,企图让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等诸多指控。对此您有何回应?
对此我无法多说,因为这纯属虚构。在主业团中,我们从不向任何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政治建议或指令:若有人如此行事,其他的成员必将反抗,因这违背我们的精神。优秀的天主教徒会根据自身的理念投票给不同的政党与候选人。我决不会告诉他们该投给谁、支持谁或推动何种主张,主业团任何成员也决不会这么做。同样也是不恰当的,如果在培育的活动中,我们营造主业团成员仅有一种合法选择的氛围,即便是间接的暗示。热爱自由即意味着热爱多元性。
在你提及的媒体中,存在着诸多假设与阴谋论,甚至指名道姓地提及某些人士,然而他们并非主业团成员。我确信他们都是优秀的天主教徒,但这些媒体纯粹是弄真相,企图将教会的机构牵扯进政治事务。
同时,我期盼世人能更理解平信徒在政治、社会及文化事务上的自主权...面对公众事务时,每位基督徒皆有责任依循教会的社会教义塑造良知,详尽了解各政党候选人的政见,思索最符合共同福祉的选择,并自由判断。正因如此,主业团的灵性陪伴工作从不干涉成员在世俗事务上的正当抉择。尊重参与政治的平信徒(无论是否属于主业团)之自主权至关重要:其是非对错应由个人承担,而非教会之责。将信徒的文化、政治、经济或社会倡议归因于主业团或整个教会,实属神职主义。
阅读 The Pillar 发表的访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