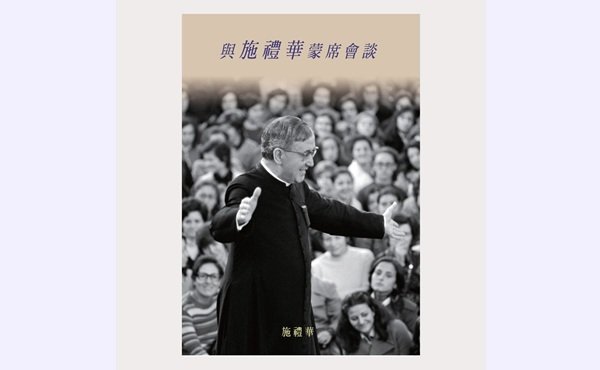《會談》一書收錄了聖施禮華與《紐約時報》、《時代週刊》及其他知名媒體記者的七場訪談,並以他最廣為人知的講道〈熱愛世界〉作為壓軸,為全書畫下句號。在訪談中,聖施禮華詳盡闡述了主業團的核心理念,深入探討其本質、精神與使命,並回顧了主業團在六十年代首次受到廣泛關注時的歷史背景與發展歷程,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時代視角。
當時,尤其是在謁見保祿六世之後,施禮華蒙席愈加堅信:若要使主業團新的法律架構方案真正落實,必須等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結束之後。他認為,稍作等待是必要的,好讓大公會議的文件與指導方針能被充分吸收,並使教宗在需要時頒布相關的施行法令。同時,他也能善用這段時間,為下一階段做好更周密的準備。
1966年,《費加羅報》(Le Figaro)的一位法國記者採訪了主業團的創辦人。此後,他又應多家歐美媒體的邀請,陸續接受了其他訪談,共計七次。[1] 到了1968年,一本名為 Conversations with Msgr. Escrivá de Balaguer * 的書出版,收錄了前述的訪談內容,以及施禮華蒙席於1967年10月8日在西班牙納瓦拉大學校園向三萬人所發表的一篇講道。這本書出版後迅速獲得廣泛迴響。[2] 值得注意的是,施禮華蒙席在書中詳細闡述了主業團的精神、使徒工作和本質特徵。《會談》在某種意義上延續了他於五、六十年代所撰寫的「書信」文獻。在那些書信中,施禮華蒙席主要向主業團成員闡明組織的制度狀況;而在《會談》中,他則面向普羅大眾發表言論,讓我們得以深入理解他的教導,並掌握他在這個教會法發展的關鍵時刻,如何呈現主業團。
在整個訪談過程中,施禮華蒙席始終以積極而謹慎的態度表達自己的立場,並刻意迴避任何爭論。他沒有觸及俗世會的發展與演變,儘管此一議題在梵二會議後的數年間已引發廣泛討論。即使在被直接問及時,他也僅表示當下並非探討此議題的適當時機,隨即轉向其他話題。[3] 我們也沒有發現他明確提及已作出尋求新法律解決方案的決定,然而,其中有多處措詞顯然受到先前所述事件與既定行動方針的啟發。
在《真言雜誌》(Palabra)的訪談中,他描繪了自1948年以來持續發展的歷史全景,將「主業團」置於基督徒靈修發展的脈絡之中,從而為日後對其會章的後續討論奠定基礎:「主業團既不是,也絕不可能被視為與教會中所謂「成全地位」(status perfectionis)的演變過程相聯繫的。主業團不是一種現代化的,或追上時代的成全地位。……由於要提供一個完備的信理解釋,需要很長時間,所以,我只想指出:除了所有人藉由聖洗聖事已領受的獻身之外,主業團無意要求成員們發任何聖願、承擔許諾,或進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奉獻。我們的協會[4] 絕對不希望它的成員為了追求成全地位而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況,或放棄與其他任何人一樣的普通教友身分。相反,主業團所希望並努力實現的,是讓每個人在各自的生活狀況中,在各自教會內和社會上的地位與條件,展開使徒工作,並聖化自己。我們不會把任何人從他的崗位抽離,也決不會把他從世界上的工作、人生目標和崇高承諾分割開來。……因此,主業團的社會現實,它的靈修精神以及它的行動,在教會的生活中屬於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徑。這一切,正在經歷一個神學性且充滿生命力的演變進程,引導平信徒在教會內全面承擔其職責,並以其專有的方式參與基督及其教會的使命。自主業團成立四十年來,這始終是天主所願意灌輸到我和我孩子們心靈中的一股恆常不變、寧靜致遠,卻又強而有力的思潮,一種渴望為天主服務的心志。」[5]
在接受《時代週刊》(Time)訪問時,他以更具體且具法律層面的角度探討此一議題。記者詢問主業團可與那些機構相比——是修會、俗世會,或其他天主教組織,如聖名會、哥倫布騎士會等?創辦人答道:「這問題並不容易回答。當人們比較以靈修為宗旨的組織時,往往失之於單單考慮它們的外表或它們的法律地位,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它們的精神,因為精神才是賦予它們生命的活力,精神才是它們一切活動的命根子。」毫無疑問,若從歷史背景加以回顧,此一言論自具深遠意義。隨後,他繼續說:「就你所提及的那些組織,我只想說:主業團與修會和俗世會是截然不同的,而與『聖名會』之類的協會則較為相似。」

他始終堅持將主業團定位於基督徒日常生活的範疇,而非視之為完美狀態或修會聖召;這一立場直接塑造了他的回答。隨後,他在不作任何比較的情況下,以極為簡潔明瞭的語言描述了主業團的特質,並避免使用任何教會法上的術語:「主業團是一個國際性的平信徒組織。有一些為數只佔很小比例的在俗司鐸,也屬於主業團。主業團成員,是生活在俗世中,從事正常工作的人士。他們不是為了放棄自己的工作,才加入主業團的。恰恰相反,他們到主業團來尋求的,正是聖化自己工作所須的靈修輔助;從而使他們的工作,成為聖化自己以及幫助他人走上同樣的途徑。他們的身份並不因此改變,他們仍舊是單身、已婚、喪偶或司鐸。他們所要做的,就是在自己的生活狀況中,為天主服務,並為世人服務。主業團對於發願或許諾毫無興趣,它要求成員,奮發努力,修務人性和基督徒的美德,在人生不可避免的限制和錯誤中,活出天主子女的身分。」在進一步闡述時,他使用了更具為技術性的語言:「主業團對於發願或許諾毫無興趣,它要求成員,奮發努力,修務人性和基督徒的美德,在人生不可避免的限制和錯誤中,活出天主子女的身分。」
他的詳盡答覆最終回到他在談及主業團時經常提及的一個現實:他深知唯有初期基督徒的歷史經驗,才是理解主業團的唯一合宜範例。「如果你要找一個容易理解的比較焦點,那麼把主業團與早期的基督徒相比較,是最恰當不過的。他們同樣嚴肅認真地實踐其基督徒聖召,誠懇踏實地追求聖洗聖事所召喚的修德成聖的目標。從外表上看,他們絲毫無異於一般公民。主業團成員,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他們像其他人一樣在俗世中工作,跟他們加入主業團前完全一樣。他們的言行舉止,毫無矯揉造作之處。他們的生活,跟其他所有願意全心回應信德要求的基督徒一模一樣,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如此。」[6]
在《會談》中,施禮華蒙席就主業團的生活、精神和使徒工作的各方面提出評論。他也回答了有關主業團在不同國家的發展、所遇到的困難或誤解,以及未來前景的具體問題。從這些答覆所呈現的主業團形象,正呼應施禮華席早期所提出的「一個有組織的精簡組織結構」(an organized unorganization)[7]。換言之,主業團是由來自不同國家、具各種社會背景的男女所組成,每個成員皆在自己的環境中,完全自發性地、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思考方式行事。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制度性的機構,主業團的根本使命在於為那些生活在世俗中,卻渴望依循耶穌基督言行的方式而行事的人,提供教義和神學上的培育,以及必要的靈修指導。[8]
主業團確實需要引導,因此亦須具備一定的組織;施禮華蒙席在《會談》中談及這點,但他始終強調,這種組織結構應維持在最低限度,嚴格規限於「不可或缺的」 [9] 範疇內。他同時指出主業團的使徒活動不僅必須具備屬靈性質,更應旨在展現「基督徒的生活觀」[10]。這些活動依照各自的使命,以不同方式致力於「幫助男女人士成為優秀的基督徒,從而在他們的日常工作中為基督作見證」[11],此即其根本目標。然而,他一再堅持,若要理解主業團活動的廣度,不能僅聚焦於教育或社會服務,即使這些工作再卓越,仍須關注參與者的基督生活本身:「主業團最重要的使徒工作,就是每位成員在日常生活中透過與朋友和同事的接觸,以自己的言行舉止作出信仰的見證。」此外,他也以類似方式談及許多非主業團成員,指出他們雖不屬於主業團,但仍以不同方式分享並受益於其精神。[12]
通讀全書,可以清楚感受到施禮華蒙席始終致力於拓展訪談者的視野。他不斷將對方的注意力由狹隘的觀點或推測性的困難,引導至主業團所展現的整體牧靈現象。在這過程中,或在他的全面闡述中,創辦人反覆強調:在世界各地,不同國籍與處境的眾多男女——包括司鐸和平信徒、單身的和已婚的——皆在主業團精神的引導下,努力在各種情境中實踐基督信仰。他似乎不僅在於使人認識主業團的存在,更在於凸顯其存在的根本意義,即天主於1928年10月2日所啟示的旨意。[13]
施禮華蒙席經常重申普世成聖的召喚,同時也刻意延展自己的省思,以彰顯這訊息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它對當代基督宗教意識拓展的貢獻。例如,教會日益成熟的願景是「由全體信友組成的一個團體」,其中,「人人分享同一個使命,而每個人應按自己的具體境況去履行這個共同的使命」[14]。這一教會觀對於理解主業團具有深遠意義。因此,教會是一個沒有任何人處於被動地位的團體,所有信徒,不論身分或處境,皆被召喚去實踐教會的使命。「因此,只要有一位誠心以基督之名生活的教友,那裡便有教會的臨在。」[15] 在這個團體中,司鐸摒棄任何形式的神職主義,他最大的榮耀在於培養所有基督徒對其個人聖召與尊嚴的意識。同樣地,平信徒亦明白自己被召去完成一項超越聖統制特別委託的使命。憑藉洗禮,他被納入基督及其教會中,並成為救主使命與生命的共融者。[16]

同樣重要的,是基督宗教對人所生活之世界價值的強調。基督徒的生命,尤其是普通平信徒的生活,正是由這世俗結構與使命交織而成。他必須在這些現實中,並在自己置身世界的存在中,視之為基督徒召叫的根本要素,而非僅僅作為一種社會事實。這一教導在《會談》中屢次展現,而在本書結尾所收錄的講道中,更以最具說服力的方式加以闡明。
這篇講道是在納瓦拉大學校園的露天彌撒中宣講的,周遭環境由樹木與建築環繞,眾多信友齊聚。施禮華蒙席在提及這樣的環境時說道:「當然,在你們的心中,透過上述的這個具體、難以忘懷的景象肯定了一個事實:日常生活的確是基督徒生活的真實「環境」。我的孩子,你們與天主的日常接觸,就在你們的同伴、你們的願望、你們的工作,和你們的感情當中。在那裡你們和基督有著每天的會面。正是在世上最物質化的生活裡,我們必須聖化自己,侍奉天主,和服務人類。
我不斷引用聖經的言語來教導這一觀點:世界並不是邪惡,因為它也是來自天主的手中,因為它是天主的創造,因為雅威眷顧了它,認為它是好的(參閱創1:7及其後)。然而,我們人類因犯罪和不忠,使世界變得邪惡和醜陋。我的孩子,不要懷疑:對你們,世上的男男女女來說,凡是藉詞逃避日常生活裡真誠的現實,都是違反天主旨意的。
相反地,你們現在必須更清楚地明白,天主召叫你們在人生平凡的、物質的,和俗世的活動中來侍奉祂,也透過這些活動侍奉祂。每一天,祂在實驗室、手術室、軍營、大學教授的座席、工廠、工作坊、田間、家庭,和在所有形形色色的工作中等待我們。要清楚明白這一點:即使在最平凡的境況裡,都隱藏著一些神聖的、來自天主的事物,只在乎你們每一個人去發現它。[17]
最後,我們必須提及他關於公務司祭職的教導,以及其在教會和各種使徒工作中的角色。施禮華蒙席再次援引他先前所提到的一個比喻,即「聖事之牆」。主業團的每一位成員,正如所有基督徒實際上都蒙召去做的——「努力在自己的生活環境中成為一名使徒,用他的言行榜樣和與他人的對話,引領人們更接近基督。然而,在引導人靈沿着內修道路前進的使徒工作中,他們會碰到一堵「聖事之牆」。若缺乏司鐸的聖化職能,平信徒的聖化使命便無法圓滿完成——只有司鐸才可以施行修和聖事、舉行感恩聖祭、並以教會的名義宣講天主的聖言。」[18] 接著,他討論了司鐸職務的一般意義[19],以及司鐸在主業團使徒工作中的角色[20],並特別提及允許已歸屬於教區的司鐸能成為聖十字架司鐸會會員的規定。
引起我的關注並展開主業團的使徒工作,並不是那些偶然發生或短暫性的情況,而是與教區司鐸的職務與生活休戚相關的,屬於持久的靈性和人性的需求。我所指的,是在教區司鐸履行其牧職的過程中,以一種絕對不影響其教區司鐸身份的精神和方式,協助他們尋求個人聖化所需的輔助。主業團精神的一項基本特徵:就是它絕不把任何人從其崗位挪開。「各人在甚麼身份上蒙召,就該安於這身份。」(格前 7:20) 相反地,它引導每一個人盡善盡美地履行本身崗位的職務與責任,以及他在教會內和社會中的使命。因此,若一位司鐸加入聖十字架司鐸會,他既不改變也不放棄他的教區聖召的任何部分。他對所歸屬地方教會服務的忠誠、他對其教區主教的從屬、他的在俗靈修生活、以及與其他司鐸的團結共融等等,均毫無改變。相反,他努力圓滿地活出自己的聖召,因為他深知他之所以精益求精,正是為了善盡他的教區司鐸職責。[21]
這些正是《會談》中的若干核心觀點。無容置疑,施禮華蒙席在1966至1968年間所接受的訪談中,關注的不僅是主業團的制度問題,更涵蓋了與整體教會生活及主業團使徒工作發展相關的諸多期望。此處所觸及的要點,在不同程度上皆與我們的主題相關。同時,它們也見證了主業團的創辦人,在等待新一輪討論展開之際,致力於將那些闡明並指引主業團期望之教會法地位改變的觀點,傳達給教會當局、主業團成員,以及普羅大眾。
此外,顯而易見,既定立場的重申及其伴隨的神學闡釋,提供了關鍵的資料與事實,促進並加速了相關思想的成熟,使得日後能夠獲致新的、最終的法律解決方案成為可能。邁向此目標的進程即將展開;事實上,它始於1969年,並開啟了一段漫長的歷程,直至1982至1983年間方告完成。
[1] 按時間順序排列如下:《費加羅報》(Le Figaro),巴黎,1966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1966年;紐約,1967年;《大學報》(Gaceta Universitaria),馬德里,1967年;《真言雜誌》(Palabra),馬德里,1967年;《泰爾瓦(Telva)》馬德里,1968年;《主日(梵諦岡)觀察報》(L’Osservatore della Domenica),羅馬,1968年。
*《與施禮華蒙席會談》(香港,清泉出版社,2025年)。
[2] 1968年,除了西班牙語原版外,還出現了義大利語、英語和葡萄牙語譯本;1969年出現了法語版,1970年出現了德語版……自那時以來,該書已用7種不同的語言印刷了41次,總印刷量達30萬冊。
[3] 參閱《會談》25。
[4] 值得指出的是,為了避免使用「俗世會」(secular institute)一詞——或「團體」(Institute),因為後者可能讓人聯想到前者——施禮華蒙席在當時開始改用「協會」(Association)一詞。他認為這樣的用法是正當的,因為依照他的主張——以及《眷顧之母》(Provida Mater Ecclesia)憲章的教導——俗世會本質上就是信友的協會。有時,他也使用「機構」(Institution)一詞。
[5] 《會談》20。他在《主日(梵諦岡)觀察報》(L’Osservatore della Domenica)的訪談中,重申並深化了相同的理念,《會談》62與66。
[6] 《會談》24。
[7] 他使用了這個詞語三次:分別是在《真言雜誌》(Palabra)的訪談、《費加羅報》(Le Figaro)以及《主日(梵諦岡)觀察報》(L’Osservatorre della Domenica)(《會談》19、35與63)。
[8] 其他類似的表達:「我的意思是:在我們的使徒工作中,我們最重視的,既不是主業團的組織結構,也不是由管理層自上而下強加的策略;而是每個人的自發性——那是由天主聖神激發引導的、自由且負責的主動行動」(19)。「主業團的主要活動,是為其成員及其他人士,提供他們在俗世中做一名優秀基督徒所需的靈修輔助」(27)。「這就是主業團主任們的基本任務:幫助成員掌握和實踐基督徒信仰,使他們完全能以個人自治的精神,把信仰具體地實現在個人的生活中」(53)。「主業團的主任們的所有活動,是以高度尊重成員職業自由為基礎的」(27)。「主業團的目標嚴格地局限於靈修範疇。它對成員提出的唯一要求──不管他們是否具有社會影響力,就是要他們竭力過完善的基督徒生活。它從來不會干預成員的工作方式,也從來不會試圖協調成員的活動,更不會利用成員所擔任的職位」(49)。「每個成員的行動是完全自由的。他自主地培育個人的良心。他在生活的各種境況中,在自己的家裏,透過聖化自己的工作,無論是勞心還是勞力的,努力追求基督徒的成全,並使他周遭的環境變得基督化」(35)。
[9] 《會談》19與63。
[10] 《會談》18。
[11] 《會談》21。
[12] 《會談》31,相同的理念亦見於其他篇章,例如41與84。
[13] 「主業團的目標是希望世界各地的廣大人士,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認識到,他們可以聖化自己的日常平凡生活,聖化他們自己的日常工作」(《會談》84)。「自1928年主業團成立以來,我不斷地宣講教誨:修德成聖,並不是少數得天獨厚者的專利。世上的一切道路,每一種生活狀況,每一種正當職業和每一項誠實的工作,都可以是神聖的」(《會談》26)。在其他訪談中也可以找到類似的措詞。
[14] 《會談》59。
[15] 《會談》112。
[16] 參閱《會談》59–62,及112中的長篇段落。
[17] 《會談》113–114。
[18] 《會談》69。
[19] 《會談》3、4、5、7、8、59。讀者亦可參閱一篇於1973年發表的講道〈永恆的司鐸〉,該文已收入《熱愛教會》,香港,清泉出版社,2025年,第67–82頁。
[20] 《會談》4、6、24、69、119。
[21] 《會談》16;另參閱69與119。他在其中探討了教區司鐸依其身分,在各種不同的團體中尋求靈修協助的自由問題(參閱7–8)。